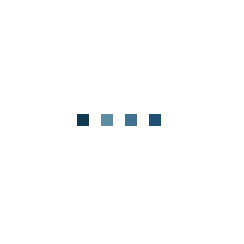林芳如/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理事長
1980年2月28日,美麗島事件受難者林義雄先生出席軍事調查庭的那天,他家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滅門血案。林義雄的母親、9歲長女、7歲的雙胞胎幼女皆身中多刀,送醫後僅長女倖存。這起悲劇因發生在2月28日,被民間視為台灣人「第二次的二二八事件」。
近半世紀過去,這場大悲劇至今只有受害者,沒有加害者。然而,改編自此案的電影《世紀血案》,竟選擇在農曆春節前召開「殺青記者會」。對比當年林家農曆過年前後所承受的壓力與痛楚,這場宣傳操作不僅恐怖,且無比殘酷。
被無視的「獄外之囚」與二度傷害
威權統治時期的「白色恐怖」除了剝奪政治犯的尊嚴、自由與生命,政治犯家屬也是長期受嚴密監控的「獄外之囚」。這起國家注視下發生的滅門血案是家屬親友心中永存的煉獄,當年許多期盼政治改革的支持者,也多表示曾經心痛至夜不成眠。如今,電影公司在年節前夕舉辦「殺青宣傳記者會」,演員們談笑風生地表示《世紀血案》的劇本「沒有意識形態」、「沒那麼恐怖」、「(拍攝時)有像福爾摩斯與華生辦案的快感」。此外,電影劇組開拍前後完全沒有與林家當事人溝通。這場宣傳記者會的安排時機,以及上述「去政治化的言論」,不僅缺乏對受難者的基本尊重,更可說是在將近半世紀後,對受害者進行了一場精準的文化暴力。
評論家蘇珊·桑塔格(Susan Sontag)在《旁觀他人之痛苦》中所警示,若我們僅將他人的痛苦視為景觀或商業素材,那便是在消費他人的苦難。儘管「林宅血案」的具體真相至今未明,但國家暴力確實存在於事件之中。電影《世紀血案》試圖將台灣社會認知的政治謀殺案進行「去政治化」的詮釋,這不僅抹除林義雄先生與其家屬當年為政治改革付出的公共性,也同時消解「世紀血案」與國家暴力的關聯。
詮釋權的掠奪:當創作者站在加害者的陰影下
這齣電影未上映就招致批評的原因,還包括導演本人是當年「警總發言人」的後代,且本片開拍竟然沒有與林義雄先生及其家屬進行溝通,其問題已非關藝術創作,而是一場權力不對等的文化與人格侵犯。影視創作雖有自由,但涉及真實的人間慘劇時,倫理邊界不容跨越。如果藝術創作可以無視家屬意願、還能抽離政治人物的政治背景,並將慘案包裝成懸疑娛樂,而宣傳時卻可高調說「改編」自「林宅血案」。那麼這種「創作自由」與當年的威權暴力又有何異?
讓記憶在尊敬裡被安放:期有更尊重的文化關懷
捷克作家米蘭·昆德拉(Milan Kundera)說:「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,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。」《世紀血案》目前的宣傳模式,無疑是以受難者的創傷,轉化為商業市場上的血色籌碼。更讓人憂慮的是,其創作過程全然忽略受害者的存在,等同再次製造失語的受害者。這將使社會遺忘「林宅血案」的沈重,並掠奪了政治受難者與所有關注此事者的尊嚴,讓台灣社會數十年來民主追求的重量輕如鴻毛。
對歷史真相的追求,是對人性尊嚴與社會文明的守護。但是在台灣,如此追求總被刻意貶低為政治清算,有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的轉型正義,讓這些激昂言論成為指責受害者的暗刺, 一再傷害她/他們與家屬的尊嚴。此時發聲,並非為了阻礙藝術創作,而是要再次強調:歷史的傷口若被當作賀歲片的布景,那麼被噤聲的歷史真相只會離我們越來越遠。
面對這部電影引發的爭議,我們期許的是,曾經為台灣政治民主化努力過的人,她/他們曾經受過的煎熬、記憶與個人尊嚴,能在當前高度民主自由的台灣受到尊重與接納。因此,在此呼籲社會大眾審視這部電影背後的詮釋霸權,因為藝術創作若無法建立在尊重之上,藝術將成為製造漠然的工具,而非將大眾轉向同理的樞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