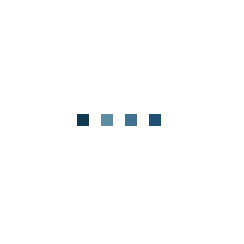吳芳銘/政治經濟觀察員
當霍諾德(Alex Honnold)徒手攀上台北101大樓,世界看到的不只是一場極限運動,而是一種制度與環境允許下誕生的「非典型人才」。這類人才的共同特徵,是長期無回報、高風險投入、孤獨準備,以及對主流價值的低度依賴。問題於是浮現:在台灣社會,為何這樣的人如此罕見?
答案並不在個人,而在整個社會系統。
台灣教育體制從小訓練的是服從、標準化與避錯能力。孩子被教導要找標準答案、追求排名及避免犯錯。在這樣的環境中,「安全」被視為美德,「冒險」則被視為不負責任。久而久之,風險被內化為羞愧,嘗試被等同於失敗。這種教育與文化環境能產出大量優秀的執行者,卻很難孕育出極限創新者。
更關鍵的是社會獎勵機制的導向。在台灣,醫師、律師和工程師等代表卓越與成功;公務員是穩定的工作;而極限運動者、非典型創業者與藝術工作者,常被貼上「不務正業」的標籤。一個年輕人若選擇長期投入高風險領域,家庭通常不是支持,更多的是焦慮。
社會潛規則很清楚:你可以優秀,但不能離群。這種價值排序,使得所有偏離主流的路徑在萌芽階段就被修正掉。
空間結構同樣重要。台灣是高度密集社會,家庭連結與社群網絡緊密,而且輿論反應與擴散快速。在這裡,人很難真正「消失」十年去磨就一件事,也難以逃離親友比較、社交評價與現實壓力。任何非典型的選擇,常被即時拉回現實的軌道。
這是一種溫柔卻持續的馴化。
而像霍諾德這樣的長期養成的極端型人才,往往成長於低干預、高自主的環境:空間遼闊、個體孤立,以及允許長時間與自己對話。他們的共同特徵是高度自律、強烈內在動機,以及對體制邊界的低敏感度。這類人需要的是長期無回饋的投入,以及社會對「不確定性」、質疑眼光的容忍與認同。
台灣恰恰相反。我們的社會培養的是「可控的人才」,不是「不可預測的天才」。制度擅長生產穩定的專業者,卻缺乏讓高風險人格自然生長的土壤。
更深一層的問題在於:即使台灣真的出現這樣的人,社會第一時間關心的往往不是他如何準備、心理結構為何,而是是否合法、有無保險,以及萬一出事由誰負責。
我們習慣於保守而優先處理風險,而非理解或認同那一份不為眾人所理解的卓越。因此,問題從來不只是「為什麼沒有攀爬101的人才」,而是台灣是否願意容許那種長期孤獨、結果未知,又極端投入的生命路徑存在。
易言之,台灣的高密度社會環境將「風險壓縮」,人才培養體系以效率與安全為核心。教育制度較追求標準化,職涯路徑高度集中於少數被認可的成功模式。另外,家庭在風險分攤中也扮演著關鍵角色,也因此成為一股保守力量。任何長期不確定、無法立即產值化的投入,都容易被視為「不負責任」或「不確定」投資的難以回報。
台灣不是沒有奇才,而是容易過早把奇才修剪成好用的人才。台灣也不是沒有天賦,而是缺乏允許極端天賦長大的文化耐性。我們建立了一個高安全、高秩序及高效率的社會,同時也形成了低冒險、低容錯與低個體空間的結構。這樣的體系可以產生大量優秀的專業者,卻難以孕育真正突破邊界的卓越人才。
攀爬台北101只是表象的課題。真正攀爬的挑戰,是制度與環境的高度。而那面高牆,至今仍然太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