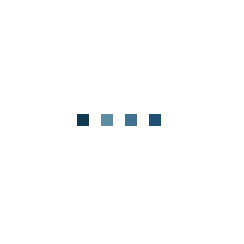林健正/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
日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遭到整肅,被指控「嚴重踐踏、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」,成為新一波軍中清洗的焦點。外界關注的,已不只是個案貪腐或失職,而是這種以「破壞制度」為名的定性,究竟是在彰顯對體制規範的尊崇,還是在進一步強化個人權威與絕對服從。
習近平近年透過大規模反腐與人事整肅,把中央軍委委員從七人清洗到僅剩兩人,且多數接任者缺乏實戰與一線指揮經驗;相對地,具有戰場經驗、熟悉台海軍事的張又俠、劉振立與何衛東等人,相繼被拉下台。
有分析指出,這種「忠誠壓倒專業」的用人邏輯,一方面削弱了解放軍的整體戰力與指揮穩定性,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決策誤判的風險。在這樣的背景下,回頭看一則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故事——魏文侯與田子方、樂羊之間的互動——反而格外凸顯出另一種截然相反的領導風格。
權力頂端真正稀缺的是什麼?
《說苑》卷八尊賢篇記載,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,田子方跟在後頭,行動從容而落在隊伍之後。太子在途中遇見田子方,下車致意,田子方仍安坐車上,只託太子轉告魏文侯在前方等他。太子覺得他態度傲慢,忍不住發問:「到底是貧窮的人可以驕人,還是富貴的人可以驕人?」
田子方回答:「貧窮者可以驕人,富貴者哪裡敢驕人;君主驕人會亡國,大夫驕人會喪家,貧者大不了轉身離去,走到哪裡都一樣貧窮,有什麼好怕的?」
在田子方眼中,真正該戰戰兢兢、如履薄冰的,恰恰是握有權力者,而非弱勢者。權位越高,越沒有任性的空間,因為一時的傲慢,不只傷及個人,更可能以亡國喪家的形式,由全體國人共同埋單。站在權力頂端的人,最缺乏的往往不是資源,而是願意聽真話的耳朵。
友士之功與友武之功
關鍵在於,魏文侯聽完太子的小報告,反應完全不同於一般權力者的本能。他不是勃然大怒、追究田子方失禮之罪,而是先對太子說:「若不是你,我哪裡有機會聽到賢人的話?」魏文侯慶幸太子把這件事告訴他,不是為了興師問罪,而是讓他有機會看清賢士的性情,也藉此教育太子。
接著,魏文侯以田子方為例,向太子說明所謂的「友士人之功」,自稱從與子方相交,君臣之間愈加親近,百姓愈加歸附,這都是與士人為友的成果。這是因為士人敢言、重義理,能為政治決策提供不同於權力慣性的價值判斷,使國家不至於只剩權術與恐懼統治。
然後,魏文侯又以樂羊為例,說明所謂的「友武之功」,提及自己想要攻打中山國,因賞識樂羊的武功而禮遇這位將領;樂羊接掌兵權後,三年內攻下中山,把戰果獻給魏國。魏文侯不僅完全信任樂羊的軍事判斷,也給出足夠空間,換來的是切實的戰略成果。
在講完「友士」與「友武」之後,魏文侯坦言,自己之所以仍覺不足,是因為尚未遇見一位能以智慧傲視他的賢者;若能找到這樣的人,自己或許就能比肩古之聖王。魏文侯不但不懼怕有人在智識上凌駕自己,反而渴望這樣的人出現,以便督促自己不斷進步。這種態度本身就是進階版的禮賢下士,不只止於招攬賢才,更歡迎賢才的凌厲眼光與嚴苛批判。
用樂羊攻中山 vs 清洗張又俠
如果把視角轉向習近平當前的軍事與用人邏輯,對比就更加明顯。魏文侯要攻中山,選擇的是以禮對待樂羊,因為樂羊有實戰本事,就給予他充分禮遇與信任,讓他以專業換取戰果;三年之後,中山為魏所有,這被視為「友武之功」。
習近平同樣把拿下台灣視為重大戰略目標,但在具體用人上,卻走向與魏文侯相反的方向。一方面,他大力推行軍中反腐與紀律整肅,把包括火箭軍與裝備系統在內的多名上將、中將拉下馬;另一方面,像張又俠這樣具有實戰經驗、在對美與台海事務上扮演關鍵角色的高階將領,也以「嚴重踐踏、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」為由遭到調查與清洗。
不少分析認為,張又俠是少數敢對習近平說真話的將領之一,他的落馬,象徵在最高軍事決策圈內,愈來愈只剩懂政治、不敢逆耳的官僚。連同有對台部署經驗的何衛東等人遭整肅,意味著在未來一段時間內,解放軍在台海議題上將面臨無人可用、無人敢言的局面。
國防與戰略研究機構學者普遍認為,這種持續大清洗,一方面削弱了指揮體系的專業性與穩定性,短期內反而降低了解放軍對台動武的能力;另一方面,決策圈失去客觀聲音,卻可能在情勢緊張時放大誤判風險。
如果說魏文侯的智慧,在於透過禮待樂羊、尊重將領專業來換取武功;那麼習近平則是在強調「軍委主席負責制」與「絕對忠誠」的同時,不斷削弱那些真正懂戰爭、懂台海的將領,使得拿下台灣在軍事上反而愈來愈缺乏可倚賴的專業支柱。從這個角度看,他在文治上排斥前朝官員及敢言的知識份子,在武功上疏遠甚至整肅可用之將,確實是背離了魏文侯「友士之功」、「友武之功」的成功路徑。
在這樣的情境下,與其問習近平還有沒有能力攻佔台灣,不如說他在追求這一目標的過程中,正透過清洗高階文武官僚,自我消耗原本有限的戰略資產,讓解放軍既更聽話、又更欠缺專業與內部制衡。這並不必然意味著他不會動武,而是意味著,一旦動武,風險與不確定性將遠高於一個尊重專業、善用宿將的領導人。
當制度被人格化之後
這一切又與制度如何被詮釋緊密相關。當代中國官方反覆強調「軍委主席負責制」,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與指揮權高度集中於軍委主席一人。這在技術層面上,原本可以是一套保障決策效率與責任集中的設計;但在實際政治操作中,它愈來愈被人格化為對習近平個人的絕對看齊,任何不同專業判斷都可能被懷疑是踐踏制度與挑戰領導中心。問題不免浮現:以後所有重大軍事與政治決定,是否都只能等待主席親自發號施令?
與之相對照的是,魏文侯在談「友士」、「友武」時,談的是如何讓賢才的道德判斷與專業能力來制衡自己的盲點。魏文侯的權力同樣集中,但他刻意把自己置於可被批評、可被「以智驕我」的位置,讓國家在制度未必完備的時代,仍有機會靠人之智慧減少錯誤。
當制度被等同於某一個人,批評被等同於破壞制度時,制度就開始空心化。表面上看,紀律更嚴、責任更清;實際上,可供糾錯的空間愈來愈小,可供賢才發揮的舞台愈來愈窄。從這一點看,習近平愈是強調責任制,卻愈是偏離了魏文侯「禮賢下士」與「尊重專業」的治國路線。
那些讓領導者不舒服的人
在多數組織裡,從來就不缺乏會說好話的人,真正罕見的是那些明知會讓領導者不快,仍願意講出專業判斷與道德憂慮的人。他們可能是對戰略冒進提出預警的將領,是對數據造假提出質疑的幕僚,是對政策風險直言不諱的專家,也是對短視政績提出批評的內部同仁。
從權力者的角度看,他們帶來的是不舒服,卻可以讓領導者多想一步、多驗證一次、多踩煞車幾秒鐘。但從整個國家或組織的角度看,他們提供的是安全閥,是防止「人主驕人而亡其國」、「大夫驕人而亡其家」的最後防線。
魏文侯所渴望的「以智驕我者」,本質上就是這一類人:在明知可能得罪最高權力者的情況下,仍選擇說出必要的真話。他之所以能成為戰國少見的賢君,很大程度上也在於他願意接住這樣的真話,並把它們轉化為治國的資本。
習近平對張又俠等人的整肅,則被不少觀察者視為反向操作:清除那些可能在戰略、作戰或對美、對台互動上提出不同意見、甚至敢當面指出風險過高的人,保留的是一批政治上更可靠、卻在戰場與決策上更安靜的將領與文官。從短期看,這或許讓權力更集中、更沒有雜音;從長期看,卻讓整個體制失去減少錯誤決策的內部力量。
結語
魏文侯懂得不以貴驕人,也願意尋找可以在智慧上壓過自己的人,於是透過「友士之功」與「友武之功」匯集傑出的文官與武將,在治國與用兵上同時展現文治與武功。習近平則在反腐與維護軍委主席負責制的旗號下,不斷收緊對軍隊與官僚體系的個人控制,排斥乃至整肅那些真正具備戰略與實戰經驗的文武高層,讓共軍在台海問題上同時面臨戰力受損與誤判風險升高的雙重壓力。
從魏文侯的標準看,一個連「友士」、「友武」都做不好,甚至把潛在良將與諫臣視為威脅的領導者,就算在宣傳上再怎麼高喊國家統一,也很難真正穩操勝算。是否具備攻佔台灣的能力,已不只是軍艦、飛彈和兵力的數字問題,更在於他是否願意讓專業與真話存在於決策核心。這一點才是古今之間真正值得比較、也最足以構成批判的分水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