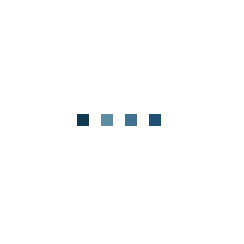林健正/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、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副理事長
談到台灣憲法法庭組成的爭議,自然讓人聯想到哈佛大學教授邁可·桑德爾(Michael Sandel)。桑德爾以公共哲學聞名,在其著作《正義:一場思辨之旅》(Justice: What's the Right Thing to Do?)中,他評判了功利主義、自由意志主義、羅爾斯與亞里斯多德的正義論,最終提出核心主張:正義不應只是價值中立的程序,而應指向目的,且必須積極追求共善,並承擔公共責任的實踐。
在另一部名著《民主的不滿》(Democracy's Discontent)中,桑德爾進一步批判當代憲政與政治哲學的現狀。他指出,當代政治正逐漸演變為一種「程序共和國」,這類政體主張在道德與宗教辯論中保持中立,試圖建立一個撇開實質價值觀的法律框架。然而,桑德爾認為這種對中立的過度執著,反而導致公民美德的淪喪,並因缺乏共同目標而加劇社會的分裂。
我們或許可以嘗試運用桑德爾的理論框架,從兩個層面檢視當前憲法法庭的爭議:其一,三位大法官(蔡宗珍、楊惠欽、朱富美)拒絕參與評議所展現的「程序共和國」困境;其二,憲政主義與法治主義在憲法架構下的真正意涵。透過這雙重視角,探討在憲政危機下,大法官究竟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。
大法官的公民責任
在這場爭議中,三位大法官嚴守法條、拒絕參與評議,一方面可以被理解為對法治良知的抗議,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個風險:如果將法治僅理解為形式合法性,而不問其背後的共善精神與公民責任,最終反而可能傷害民主憲政的根基。
三位大法官主張,依修正後《憲法訴訟法》,憲法法庭未達最低十人評議門檻,因此未依法組成,自始欠缺審判權。在這樣的理解下,她們拒絕加入評議,並在庭外公開意見中宣稱,由另外五位大法官作成的判決欠缺正當性。
與此同時,另五位大法官為避免憲法法庭長期癱瘓,決定不將拒絕參與評議的三人納入現有總額,以維持解釋權與人民訴訟權的行使,並在判決理由中指出:若將三人納入計算,法庭人數就持續不足,將嚴重妨礙憲法保障機制的運作。
若套用桑德爾的問題意識,關鍵焦點不僅在於三位大法官對「依法組成」的法律見解是否正確,而是在重大的憲政危機下,大法官如何理解自身的角色與公民責任:是否只要自認立場是嚴守成文法門檻,縱使憲法法庭已被癱瘓,她們仍可不必考量這件事對台灣社會共同體與權利保障的實質影響?
以桑德爾的語言來說,大法官的職務不只是套用程序規則的技術官僚,更是一種植根於命運共同體的公民角色,肩負維護憲政秩序與共善精神的使命。在這個期待下,完全退到形式法條後面,將自己定位為純粹的程序執行者,本身就會招致質疑:這究竟是出於良知的堅持,還是一種迴避實質責任的退場?
程序共和國的困境
三位大法官公開自我定位為:既然《憲法訴訟法》修正條文已經公告生效,憲法法庭就必須先服從該法對組成與門檻的規定;在沒有先宣告修法違憲之前,自己不能逾越憲訴法的規定參與評議,因此唯有選擇拒絕加入憲法法庭。
這是一種極端強調「法律優位」與「程序中立」的姿態,恰恰落入了桑德爾所批判的「程序共和國」窠臼。若從桑德爾的立場加以檢視,就會衍生兩個層次的批評。
第一,這種自我理解不符合中立的原則。表面上看似依法行事,實際上卻等於接受了立法院藉由修法重構乃至癱瘓憲法法庭的效果,並在客觀上站到了改寫權力分立架構的一方,只是將這個實質的選擇隱藏在程序語言之後。
第二,這種姿態可能削弱公民對憲政體制的信任。公民眼中看到的,不是願意在憲政危機中承擔共同體風險,並清楚說明自身在多重義務間如何權衡的大法官,而是以技術理由拒絕面對憲政危機的被動中立者。
這兩點恰恰呼應了桑德爾對「程序共和國」的批判:當民主體制只剩規則與程序,卻缺乏對德性與共善的追求,最終將導致公民對制度的道德認同徹底流失。
良知抗命或責任退位?
站在桑德爾的框架,我們可以公平承認三位大法官的一點:她們或許真誠相信,自己的退場是以「守法」方式向社會示警,指出立法院的修法造成嚴重的體制矛盾,使憲法法庭在法律技術上陷入失序的狀態。從這個角度看,她們的拒絕參與評議可以被解讀為一種「象徵性的警鐘」,試圖喚起對立法院修法正當性的反思。
然而,令人更關心的是:「這樣的抗議行動是否有助於共善精神與民主憲政原理?」如果其結果是憲法法庭長期停擺,人民訴訟權實際無法行使,憲政秩序出現的空窗又被立院多數持續濫權所利用,那麼即便其動機在於「守法」,效果卻是在加深共同體的憲政危機,這就與桑德爾所強調的「制度與職務應朝共善與公民德性負責」的方向背道而馳。
在評價「法律優位」與「倫理良知」衝突時,從桑德爾的視角,會存在以下三個值得關注的關鍵因素:
第一,就法的層級與正當性基礎而言,要先釐清被遵守或被抗拒的是什麼規範:是明顯不義、侵害基本人權的法律,還是主要屬於程序或技術層面的瑕疵?越接近保障人格尊嚴、基本自由與平等核心的規範,越能支撐「倫理良知」優先的立場;相對而言,若爭議多半是程序門檻,則較難正當化全面退場。
第二,就抗拒行為對共善的實質影響而言,不能只看個人是否道德自洽,還要評估對整個共同體的後果:公民不服從或官員拒絕執行命令,究竟是促成公共辯論、推動較為正義的改革,還是導致制度全面失靈、讓弱勢承擔其成本?如果良知抗命只是象徵性的自我潔淨,卻讓制度更傾向不義或失序,那麼在桑德爾看來,這更像是一種「道德潔癖式的退位」,而非負責任的共和德性。
第三,就行為所展現的公職德性而言,大法官不只是個人道德主體,也代表共同體行使權力,其良知選擇必須同時考慮職務義務與憲政秩序。這樣的決定,究竟是願意為共同體承擔風險的勇氣,還是規避難以承擔的政治責任?相關行動是否伴隨清楚的公共說理,而不是僅僅躲在抽象的「依法」或「良心」的修辭背後?
如果把這些標準疊加到當前憲法法庭的案例上,可以說:在桑德爾眼中,三位大法官的選擇更接近「程序共和國的忠誠官僚」,而不是「願意背負共同體命運的共和公民」。她們以法治之名退入中立,卻讓憲政與共善的重擔落在其他五位大法官與社會力量的肩上,成為貧瘠民主的一則鮮明註腳。
憲法的實質優位
從桑德爾的視角出發,我們可以將這場爭議置於更廣闊的框架中:憲法不應僅是條文本身,而是體現一個共同體對共善與正義的自我理解。憲法第78、82、171、172、173條,正是讓這種自我理解在具體案件中能夠「活化」的制度工具。
憲法高於法律不僅是規範位階的宣示。憲法第171條明言「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」,第172條則對命令作同樣規定,並由第78條與第173條授權司法院(憲法法庭)作出最終解釋。
換句話說,憲法之所以具有優位性,係基於它承載了關於國家存在目的、基本權利與權力分立的共同善圖像,而法律只是具體化這個圖像的次級規範。因此,「憲法」不應被窄化為純文字,甚至立憲當時的主觀意圖,而應理解為一套由基本權利、權力分立與各種指導原則所構成的規範體系,必須隨著社會實踐與公共辯論,持續落實憲法精神與立憲目的。
憲政精神與目的論
若套用桑德爾推崇的「目的論」視角,嘗試走出「程序共和國」的死胡同,邁向負責任的憲政實踐,我們能更清晰地理解憲法第78、82、171至173條等相關法條的互動。
第一,憲法第78、173條的目的在於賦予司法院解釋憲法與統一解釋法律、命令的權限,並確認憲法應由司法院解釋。這使憲法法庭並非只是技術性的「規則仲裁者」,而是在面對權利衝突與權力爭議時,負責把爭議點提升到共善層次加以說理的機構。
第二,憲法第82條規定「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」,表面上給了立法者相當大的組織形成空間。然而,在第78、171、173條的結構下,立法裁量空間並非無限,它仍須服從憲政目的。若組織法使憲法法院實質無法履行解釋憲法、保障權利的功能,就違反憲法授予司法權的目的,應被視為違憲。
第三,憲法第171、172條把「抵觸憲法」直接連結到「當然無效」,並由司法院作出最終判斷。這不只是形式上的無效宣示,更包含一項實質正義要求:當法律與命令在正義上與憲法精神發生衝突時,司法不能只做中立的執行者,而有責任回到憲法所體現的共善精神,對「惡法」說不。
憲政主義 vs 法治主義
傳統上,憲政主義強調憲法優位與權力分立;法治主義則強調依法行政及依法裁判。在桑德爾的視角下,這兩者應透過「目的論」進行調和,用上述憲法條文重寫這場爭論。
首先,憲政主義不是任意凌駕法律,而是憲法授權的審查責任。憲法第78、171、173條合起來,就是要司法去判斷:某一法律條文是否背離憲法所體現的共同善與權利結構。
其次,法治主義的「依法」,必須理解為「依合憲之法」。若修正後《憲法訴訟法》第30條這類組織條文,導致第78條所保障的憲法審查功能無法實現,則在第171、172條架構下,該條即為無效或不應適用;此時「法治」要求服從的對象,不再是第30條本身,而是經憲法審查後的憲政秩序。
宣告第30條違憲、避免憲法法庭被癱瘓,並不是「超越法律」,而是在履行憲法授權的憲政職責。這與桑德爾反對「價值中立的法治」的立場一致:法治不能被理解為對任何成文法的無條件遵守,而是對一套經公共理性與憲政結構認可的正義負責。
再以「現有總額」解釋為例:在維持憲法審查功能的前提下,對相關條文做出「功能維持優先」的解釋,正是以憲政主義校準法治主義,而非在兩者之間做二選一。用桑德爾的語言來說:真正的法治,不是躲在條文後面宣稱中立,而是願意在憲法精神與共善的光照下,做出能向公民清楚說理的價值選擇。
結語與反思
對重視憲政價值的社會而言,當前憲法法庭的爭議無疑激起許多反思。拋開「惡法亦法」與「惡法非法」的粗糙對立,回到憲法文本與共善精神,我們可以歸納出幾項重點:
一、憲法的優位,不只是位階宣示,而是對法律提出一個實質正義標準:凡破壞憲法所體現之權力分立、基本權利與共同善者,皆不得以「惡法亦法」之名獲得服從。
二、憲政主義透過第78、173條,將此標準具體化為「司法院解釋憲法」的責任;法治主義若要在此框架下成立,只能被理解為「遵守經憲法審查確認之法律秩序」,而不是盲目尊重任何立法產物。
三、在憲法法庭組成與評議門檻爭議中,應以第78條保障的釋憲機能為核心,對第82條授權的組織立法與憲訴法條文,做出使憲法法庭得以運作的目的論解釋,而非讓技術性條文自我矛盾地摧毀憲法自身。
四、大法官在憲政危機中的角色,不應是躲在形式法條後面的「程序執行者」,而應是願意承擔共同體風險,並在多重義務間清楚說理的「共和公民」,避免民主體制淪為桑德爾所批判的「程序共和國」,只剩下規則與程序,而缺乏對德性與共善的追求。
總而言之,桑德爾的公共哲學提醒我們:真正的正義實踐,永遠不可能是價值中立的,而必須是一場指向共善、願意承擔公共責任的思辨之旅。憲法法庭的爭議,正是這場思辨之旅中的重要一站,值得我們深刻反思法治、憲政與共同善之間的深層關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