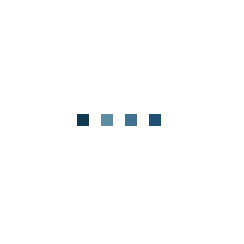那天我其實是休假。照理說,休假就該在家當一坨沙發馬鈴薯,滑手機滑到懷疑人生,頂多出門買杯咖啡,假裝有在生活。但偏偏那天的行程不是「下午茶」,而是Alex Honnold(霍諾德)要挑戰徒手攀登台北101。
這其實是攝影記者的宿命,你一旦聞到「歷史現場」的味道,腦袋就會自己把鬧鐘上好,然後身體會自動把器材扛上肩——有沒有錢先放一邊,反正很多時候,我們就是「沒錢也會做」。
一開始我們原本想說去象山拍。象山熟嘛,101也熟,站高一點俯拍,畫面看起來比較漂亮。但前一天我跟主管在閒聊時,他提醒我不要上象山,因Alex是從101的東南面上去,面向松智路那一側,轉角就是信義路那邊。如果你上象山,拍得到是拍得到,但會很遠,只剩一個小小的人影在牆上爬,群眾加油、互動、細節都拍不到。
我腦袋也先演了一輪:在底下先拍一段,等他爬到一定高度,我再衝象山補遠景——但很快就推翻。象山上下至少半小時到四十分鐘,Alex Honnold(霍諾德)的速度又快,加上人多、機車也不能亂停,你光卡位就可能被人潮吞掉。最後我們決定:就在101一樓周邊,松智路那個角,直接拍。
器材怎麼帶?我帶了一支200-500mm的大砲鏡頭,再加1.4的加倍鏡。算一算,最長等於可以拉到大概700mm。另一個同事也很硬派,他除了帶200mm+1.4倍加倍鏡,還另外扛了一支600mm的定焦大砲鏡頭。
更好笑的是,我不只帶鏡頭。我還得帶腳架,因為那種長焦不架起來根本沒辦法;還帶推車,因為器材太多,移動像搬家;而且現場人潮一多,你想要挪位置,推車就像一艘小船,在肉身海裡硬開航道。
我那天五點起床,六點就到現場。我得早點去觀察角度、確認位置能不能拍、管制怎麼走。六點開始就有管制了,101樓下有區域不能進,但信義路那些路段車還能動。六點多現場已經有民眾在卡位,旁邊的那棟樓還掛出加油標語,寫著「Alex你可以的」跟「GoAlex」。那畫面很像演唱會開場前的應援,但主角不是偶像,是一個準備搏命往上爬的人。
我到的時候其他媒體還沒來,後來電視台、平面媒體才陸續進場。我的位置還算不錯,同事比較機動,但他從側面拍到很多更震撼的畫面——尤其是國旗在飄,背景又是天空,那種高度感一下就出來。我這邊角度比較「建築感」,天空少。
後來我才知道一件事。101那邊原本的旗子不全是中華民國的國旗,有的是其他國家的國旗。101董座賈永婕那天刻意把它換成五面中華民國國旗,因為Netflix直播,全世界都在看——你不可能不看到。這招我看完只想說,很聰明。你在直播裡不太可能臨時「調角度」把旗子藏起來,他把五面國旗掛上去,等於直接讓全世界看到,這是台灣、這是台北101、這活動在這裡發生。
我在現場會緊張嗎?會,當然會。但恐懼倒不多。有人的老婆在旁邊看得手腳冒汗,她是真的怕;我反而是那種「專業訓練把情緒壓下去」的狀態——新聞現場碰到重大事件,你不能讓恐懼左右判斷,因為你一失誤,畫面就沒了。
而且我腦袋一直浮現一個影像──以前美國911事件那個「有人從上面掉下來」的畫面。說穿了,我去現場,除了覺得是台灣重要的歷史時刻,我也預想:萬一真的發生不幸,我一定要拍到。這聽起來很冷血,但這就是攝影記者的責任。
現場也有人問我,怎麼不用空拍機?我只能說,別鬧了。那邊是航區,就算申請也不一定會過;就算過,我也不會飛,因為那會干擾霍諾德及製作團隊。人家自己就有空拍跟直升機,你再飛一台上去,真的不是「加值」,是「添亂」。
我全程幾乎都盯著現場,沒時間看Netflix直播。霍諾德爬得很快,爬到一定高度後,我得一直往後退、一直移動角度,不然你鏡頭裡只剩他的屁股。我帶著一堆器材,又要在人群中硬擠,動作一猶豫就沒角度;你移動的同時又怕錯過重要瞬間,因為他速度真的太快。
我一路往後挪,挪到信義之星社區附近,距離大概兩三百公尺上下。大砲鏡頭這時候就派上用場,鏡頭裡很清楚。剛開始我也擔心他會失手,但他爬了三分之一後,我就看得出來,他遊刃有餘。他會跟101裡面的人互動、打招呼,底下群眾也和他在互動;到六十樓他太太出現,他那個笑容一看就知道,他很有把握。
我後來看他爬「酋長岩」的紀錄片才更確定,那個難度比101恐怖太多。101是規律的結構,動作會重複;酋長岩是隨時要應變,抓點踩點小到可怕。以難度滿分一百來說,我甚至覺得101可能只有七十左右。
還有個細節我覺得很值得講,現場我看到國旗的方式,其實是透過玻璃反射。我的角度沒辦法看到國旗跟他貼得多近,同事的角度比較正。當下在工作狀態,情緒被壓著,我沒有「起雞皮疙瘩」那種感動;反而是回家看Netflix、看媒體重播,我真的感動到哭了好幾次。
為什麼?不是因為我突然變文青,是因為我覺得台灣這個小小的地方,被打壓這麼久,竟然可以用這種方式被全世界看到。那天Netflix的點擊好像在很多國家都衝第一。我覺得這比砸錢做什麼廣告有效太多——你讓世界看到台北101、看到信義計畫區、看到台灣的街景,看到「台灣真的在這裡」。
我甚至覺得霍諾德很像台灣,小小的一個人在101大樓,很辛苦地往上爬,面對旁邊巨大的壓力,但還是想被看見、被接受。這種「以小對大」的感覺,說真的,太容易有共鳴。
現場我印象最深刻的畫面,除了攀爬本身,還有他跟大樓裡的人互動。有一張照片我很喜歡:大樓裡面有個男生拿手機在拍,表情嚇到嘴巴張超大——那種「我今天上班上到一半,突然看到有人在窗外爬101」的震撼,超真實。
我們從早上六點一路站拍到快十一點。雖然累,但我一點都不後悔。因為我後來看紀錄片才更理解,很多酸民會說他只是為了出名、只是膽大不怕死,但其實他花了十年、甚至更久在做精密計算,筆記密密麻麻,整件事是「一關過一關過」的專業,而不是心血來潮。
而且101這一次成功,也不是他一個人,他的團隊、攝影團隊、101團隊、台北市府各單位、Netflix製作,全都要精密計算,還要有勇氣。風險當然存在,只是他們把風險降到最低;真出意外,就是命——這句很殘酷,但現場就是這樣。
我甚至因為這件事跟朋友吵起來。有人說賈永婕就是花瓶、藝人,我反問:人家做成了、有勇氣,你給個掌聲很難嗎?就算他有運氣又怎樣?你敢不敢做?她其實可以不賭,繼續當「美美的花瓶」也不會影響她的職位,但她賭了這一次,台灣被世界看見,這筆帳怎麼算都是台灣賺到。
所以那天我扛著700mm大砲站在街口,從清晨守到中午,拍到腰酸背痛,其實只是在做一件很單純的事,把一個「台灣重要的moment」留下來。
攝影記者有時候很像被詛咒——你明明休假,卻會自己走到現場;你明明很累,卻會在按下快門那一刻覺得,好,值得。(本文內容由當事人口述,AI協力完成,經編輯核實無誤。《狗仔回憶錄》每逢週六更新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