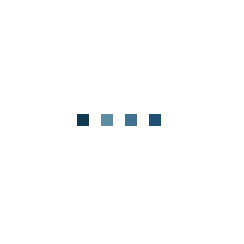林忠正/經濟學博士、前中研院研究員
2025年,川普重返白宮。就任後短短三個月,美國再度對中國、墨西哥、歐盟全面加徵關稅,並揚言「要讓美國重新掌控自己的財富與工廠」。華府重拾關稅與貿易壁壘的景象,宛如歷史重演。這一幕讓人想起三百年前歐洲各王國的經濟哲學——重商主義。
事實上,川普的經濟觀念並非創新,而是一種「歷史復辟」。他以民族利益為核心,以貿易順差為榮,以關稅與制裁為武器;這與17、18世紀歐洲國家在重商主義時代所奉行的策略,驚人地相似。
一、重商主義的誕生:國家為貿易而生
16世紀的歐洲,正值民族國家崛起與地理大發現的交錯時代。國王們意識到,國力的基礎不僅是軍事,更是財富。金銀被視為國家富強的象徵,出口多於進口、積累貴金屬、保護本國工業成為最高原則。這便是「重商主義」的誕生背景。
重商主義的核心信念簡單而殘酷:世界的財富是有限的,一國的利益必然是他國的損失。因此,歐洲各國紛紛推行高關稅、出口補貼與貿易壟斷政策。法國的柯爾貝爾在路易十四時期強化國營工廠與出口導向產業;英國則頒布《航海法》,要求殖民地的貿易只能經由英國船隻與港口完成。
在這種制度下,殖民地被迫成為母國的原料倉庫與市場,貿易戰、殖民戰爭也接連不斷。英、法、荷、西之間的競爭和戰爭,從歐洲蔓延至印度洋與加勒比海。可以說,重商主義不僅塑造了近代國家,也孕育了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全球秩序。
二、重商主義的崩壞與亞當‧史密斯的反擊
到了18世紀末,重商主義開始顯現疲態。國家干預過度、貿易壟斷導致效率低落,社會財富集中於少數特權商人與貴族手中。1776年,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‧史密斯出版《國富論》,對重商主義發動理論革命。
亞當.史密斯這個經濟學之父指出,國家若一味追求出口與貿易盈餘,反而會破壞市場的自然秩序。真正的富裕,來自個人自由追求利益的總和,而非國王的金庫。這一觀念使經濟思想從「國家主義」轉向「市場自由主義」,開啟了自由貿易的時代。川普可能沒有讀過《國富論》,他經營不動產事業的有限歷練,很可能讓他相信個人的談判技巧和手段是嬴得買賣的勝敗因素,而不是市場力量!也因此,他個人自然是「強人政治」的信仰者!
19世紀的英國藉自由市場與工業革命成為「世界工廠」,似乎證明了史密斯的預言:市場比國家更能創造繁榮。重商主義從此被視為過去的遺跡,直到21世紀,一位來自紐約的商人總統再度讓它復活。
三、川普的「美國優先」:現代重商主義的回歸
川普的經濟政策與三百年前的重商主義有著驚人的相似性:
1.高關稅與保護主義:
他以「貿易戰」為主要工具,對外課稅、限制進口、扶植本國製造業。這與柯爾貝爾的「出口導向」政策如出一轍。
2.經濟外交的交易化:
在川普眼中,外交是「生意」。他要求北約盟友分擔軍費,與日本、韓國重新談判貿易協定,對中國實施科技封鎖與投資禁令。這種以經濟作為外交武器的作法,正是重商主義時代的政治邏輯。
3.零和世界觀:
川普視貿易逆差為國家被「剝削」的象徵,主張只有美國贏、別國輸的貿易才算公平。這正是重商主義的本質:財富有限,非我即敵。
不同的是,川普的重商主義披上了民主政治的外衣。他不再以王權名義推動經濟政策,而是以選民的焦慮為基礎,將保護主義包裝成「愛國主義」。這使他既能動員工人階層,又能挑戰全球化體制。
四、重商主義的復活與全球化的反動
21世紀的世界經濟早已高度全球化,生產鏈跨越國界。任何一部iPhone、一台特斯拉,零件都來自十多個國家。這樣的分工體系下,川普式重商主義的回歸看似逆流而上,卻反映了全球化的深層裂痕。
自由貿易確實帶來整體繁榮,卻也製造了內部不平等。美國中西部製造業的衰落,使藍領工人感覺被全球化「拋棄」。川普正是利用這股怨氣,將「經濟民族主義」包裝成一場對外的經濟戰爭。
然而,重商主義在21世紀的侷限也十分明顯:(1)關稅提高雖能保護特定產業,但也推高通膨與消費成本;(2)全球供應鏈因政治干預而失序,效率下降;和(3)盟友被迫在經濟戰之間選邊站,削弱美國的國際信任。
換言之,川普的「美國優先」或許能短期提振國內信心,卻可能長期削弱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領導力。
五、結語:古老的幽靈,新的戰場
重商主義從未真正消失,它只是以不同形式潛伏於歷史深處。每當國家面臨經濟焦慮、社會不安或全球競爭時,重商思維便會重新浮現。
川普的經濟民族主義,既是對自由貿易的反動,也是一種歷史的回聲。三百年前,重商主義造就了歐洲的帝國時代;今天,它在美國的白宮裡以民粹之名復活。
亞當‧史密斯曾警告:「當國家為貿易而戰,人民的自由將首先被犧牲。」川普的「美國優先」正提醒世人:經濟民族主義或許能贏得選票,但也可能讓世界再次陷入以利益為戰場的惡性循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