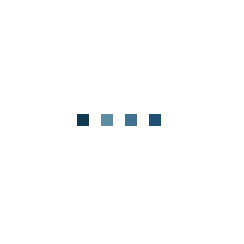近年來,陸續幾部有關228、白色恐怖的電影或劇集,敘述著同時代的人事物,不同的故事軸線有著不同的敘事安排。《大濛》應該是最適切的一部創作,故事大綱來自嘉義的少女阿月,有個閱讀左傾書籍的哥哥,在被極權老大哥槍決後,阿月隻身北上想把哥哥屍體帶回嘉義。故事軸線很簡單,但劇組非常用心,把白色恐怖期間,許多受難者的故事、受難者家屬的口訪、解密後的檔案,透過田野調查,一一寫入劇情。這根本不是戲劇,是活生生的台灣近代史。
1947年發生228事件,國民黨政府進行全島大清洗,社會瀰漫著高壓統治下詭譎的氣氛,1949年5月20日臺灣省政府與警備總部實施全島戒嚴,透過《懲治叛亂條例》、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》、《刑法》內亂罪等三大惡法,處置對政治不滿的異議者,只要有左傾、共產思想,只要對國家元首與政府有所批評,那就被扣上共匪、叛亂的罪名。以老大哥警備總部為首的國家機器,就展開逮捕、刑求,不顧法律程序也不管司法正義,冤獄、冤死遍佈全台灣。
白色恐怖(White Terror)一詞,來自於法國大革命時期,保守的波旁王朝保皇黨對激進的雅各賓餘黨採取報復行動,因波旁王朝以白色為代表色而為名。台灣歷經這段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,完全不准討論,所有受難者只能在暗夜中哭泣。比起喬治歐威爾《一九八四》的老大哥、法國或其他國家白色恐怖的殘暴,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,以及1991年6月3日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》廢止,台灣才算脫離白色恐怖的陰影壟罩。
《大濛》所蒐集的田調故事,只是冰山一角,還有更多受難者家屬的苦痛沒有被社會大眾所周知。根據曹欽榮在2017年出版的《自由遺產:台灣228、白恐紀念地故事》附錄一《白色恐怖被槍決部分名單》,受害者共列名1,099位,確知執行槍決者1,076人。但,實際數字難以考證,許多研究陸續提出數據分析,促轉會曾以「受裁判人」為對象(判死刑比例約為一成多),提出13,268人或13,683人次(有人遭受一次以上的裁判)的數字;也有數萬人,甚至10多萬人的估計。然而,實際受難者到底有多少?還有多少黑數?許多檔案已遭到銷毀,包括國安局、調查局、國民黨、前警總,以及其他監控倖存檔案,並未完全公開透明,很多問題的答案依然未知。
解嚴後2年,1989年電影《悲情城市》衝破不可公開討論的禁忌,影視圈逐步開始挖掘這段歷史的吉光片羽,並將真實故事轉譯成IP作品。包括:《香蕉天堂》、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、《超級大國民》、《好男好女》、《天馬茶房》、《淚王子:清泉一村的故事》、《被出賣的臺灣》、《阿罩霧風雲2:落子》等。近年有更多作品出爐,例如:《返校》、《流麻溝十五號》、《星空下的黑潮島嶼》、《餘燼》,以及正在上映的《大濛》。看似作品非常多,但在迷霧中,我們離陽光普照還很遙遠。
總是有人高喊要被害者「走出悲情」,但那是最廉價的反省,因為失去至親好友的傷痛是永遠走不出來的,沒有人有資格要被害者忘記傷痛,只有讓最完整的真相出爐,那才是「正義」。其中,最應該被檢視的就是「加害者」,然而,阻擋這一切的就是「加害者」,他們不願意被公開討論,也間接導致在眾多影視作品中加害者的角色總是很模糊。我們是很難定義「加害者」到底是誰?不過,「特務治國」是最接近的答案之一。
在「特務治國」的宰制之下,白色恐怖是不分族群、省籍的苦難,然而,本省/外省就等於受害者/加害者的二分法切割是錯誤的方式,那是統治者的詭計,目的就在有助於凝聚其支持者,以利其阻擋轉型正義的制度建立工程。從影片的呈現來看,《大濛》似乎試圖用角色形塑,讓苦難跨越族群與階級的存在,來破解這樣的設定。
以《大濛》為例,趙公道、二雄、山東籍攤販、極樂殯儀館的老王等,他們全都是生活在底層的外省族群,各自有著對生活艱難的承受、來自心底正義的呼喚、經濟壓迫下的委屈、對極權權勢的無奈,然而,他們展現生活在極權統治下的勇敢,在大時代下不得不低頭的韌性,面對正義不存在的掙扎,以及在人性善惡之間良心受創的苦楚。特務范春是另一種類型,甘為老大哥的附庸,並為極權體制服務,最終在黨國庇護之下,經商成功,成為大時代下的勝利者。
韓國影視創作者令人欽佩,諸如: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、《正義辯護人》、《總統的理髮師》、《首爾之春》等描述政治鬥爭、無情屠殺與不公不義壓迫的電影或劇集。韓流崛起的強悍力量,主因就是勇敢的碰觸敏感禁忌議題,他們一把掀開統治者最醜陋的真面目,轉化成影視作品,震攝人心、撼動社會。那台灣呢?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非常多,成千上萬的受害者,有許多非常殘忍、離奇、荒謬的故事文本,這些都是台灣社會不分族群的集體記憶;台灣已經慢慢走出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」的時代,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影視作品出爐,讓台灣社會有更多自我省思的機會。
每個人終究都是別人眼中的風景,當雲霧散去,如果沒有讓陽光普照,黑暗就不會離開,我們就不會看見任何風景,包括:別人與自己,若是如此,那每個人都不會再有存在的意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