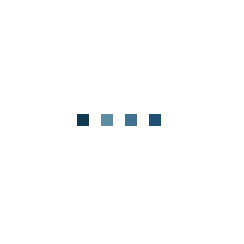張娟芬/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理事長
一、 緣起
2024年,憲法法庭受理死刑案件,這是史上第四度解釋死刑相關的憲法爭議。就在那時,我從司法院網站上讀到第一次釋憲的聲請書,也讀到黃樹明的故事。
釋字194號的聲請書由黃樹明自己具名。他說他為了治療胃病,開始使用嗎啡,不幸成癮,無法戒除。他有一個一同當兵的朋友也是這樣為了治病而染上毒癮,兩人有時互通有無,不料這朋友吸毒被捕,警察要他假裝向黃樹明購買毒品,於是就成了販毒的罪證。黃樹明被「釣魚」了。
黃樹明聲請釋憲,有幾項訴求。
第一,《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,販賣毒品唯一死刑,黃樹明主張此法違憲。他提出兩個論據:(1) 販毒情節不分原因與輕重,一律科處死刑,違反憲法第七條的平等權。(2) 唯一死刑「率爾剝奪至高無上之生命權,毫無彈性保留可言」,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的必要原則。
第二,他的案件以他的自白為認定有罪的唯一證據,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6條,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。這一點可以細分為幾項:(1) 警察刑求黃樹明,逼他承認販毒,自行為他製作一份「承認」的筆錄,並且在他雙手銬住時強拉手指捺下指印,所以他的「自白」上留下一個長形有拖曳痕跡的指印。(2) 銜命做餌的這位朋友也被警察刑求,不得不指證黃樹明販毒。檢察官偵訊與法院審判時,他都翻供說那是因為警察刑求,但法院不採信。(3) 黃樹明沒有與共同被告對質詰問的機會。
除了主張法律違憲之外,黃樹明也許更想說的是,判他有罪的這個判決是錯誤的、違憲的。他所主張的諸多冤情——刑求取得自白、以自白為唯一證據、共同被告的自白未經對質詰問——每一項都在後來司法改革的過程裡,集結眾人之力才得以改正;也就是後人跌倒之處,都留著黃樹明乾涸的血痕。
他提起釋憲時,大法官只做「法規範審查」,不做「裁判憲法審查」,也就是大法官只管「這條法律有沒有問題」,不管「這個判決有沒有問題」。黃樹明對自己案件的不平之鳴,根本不在大法官的視野或職權之內,2022的《憲法訴訟法》才將裁判憲法審查納入憲法法院的職權。不過,黃樹明像所有小老百姓一樣,只要有機會申冤,管他職權內職權外,何妨全部說一遍。
於是我把黃樹明的事情寫進了法庭之友意見書:「有些人支持死刑的理由是『一命償一命』。他們應該會同意,這六位未曾殺人的被告不應該判處死刑。如果台灣的違憲審查制度有一本帳冊記明大法官的功過,上面應該有這六條人命的負債。」
2024的釋憲,最後仍是一個無言的結局。憲法法庭以113年憲判字第八號判決宣布死刑有條件地合憲。憲判八提出的幾種限縮死刑的方法,幾乎都已經是死刑判決實務的現狀;而「死刑是否違憲」的關鍵性問題,大法官躲開了[1]。大法官做出一個對現狀不生影響的釋憲,只能說自視甚低。這時我想起了黃樹明,第一位提起死刑釋憲的人,他會不會有家人呢,那裡還有更多的故事嗎?
我搜尋新聞資料庫,想碰碰運氣。出乎我意料的是:他竟然沒死!1983年之前與之後,都有他吸毒被抓的新聞,他竟然沒死!於是我找到釋字194號的國家檔案,打開第一次死刑釋憲的後台。
二、 審理大法官組成及運作
黃樹明的聲請書於1983年提出,實際進入審查會議時,是1985年三月。當時的違憲審查曠日廢時是常態[2],本件耗時555日,並不特別長。審查時,第四屆大法官已經進入最後半年任期。
當時大法官一任九年,可以連任。最資深的林紀東已經當了三任。從第三屆連任至第四屆的是陳樸生、陳世榮、范馨香、翁岳生四位,第四屆上任的有七位,最後李鐘聲、馬漢寶、楊建華、楊日然四位是1982年遞補的,因為有幾位第四屆大法官在任內病逝。最資深的已在位26.5年,最資淺的也近三年,大家都不是新手。就年紀來看,七字頭的四位,五字頭的四位,剩下八位是六字頭。最後遞補的四位年紀較輕,可以看出八〇年代初期避免老人政治的微弱企圖。年紀與資歷不成比例的是翁岳生,他在第三屆被提名時還不到四十歲,第四屆只有楊日然比他年輕一歲,但第二年輕的翁岳生已經是第二資深的大法官。
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現實裡仍然很重視省籍,16位大法官中有三位台籍:陳世榮、翁岳生與楊日然。不僅「外省/台籍」之分很重要,「外省」之中的各省分布也很重要,例如四川籍的楊與齡就因「西南地區」的名額入選[3]。第四屆大法官初上任時,《聯合報》報導:「就籍貫之分而言,當然無法涵蓋每一個省份,但已盡量使其具備地區代表性,所屬籍貫涵蓋達十二省之多[4]」,可見省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。戒嚴時期並沒有落實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,大法官人選由「五人小組」提名,包括副總統、監察院長、司法院長、總統府秘書長與國民黨秘書長,徵詢意見時常由國民黨人士出面[5],決定後提報國民黨中常會,得到認可以後經總統核可,最後由監察院行使同意權;但「五人小組」同意就是定案了,監察院只是形式。例如第四屆大法官名單經過國民黨中常會同意,媒體就當作定案報導了[6]。此一流程直到1994年才不再經過國民黨中央黨部[7]。根據馬漢寶的說法,第四屆只有他一人不是國民黨黨員[8]。
事實上,以政治力量控制司法,是國民黨自1929年即開始施行的政策,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「司法官吏之任用,必須以深明本黨主義為標準[9]。」「黨化司法」在初期公然為之,例如姚瑞光的口述歷史即寫到:「適中央黨部倡導『黨化司法』,遂經中常會通過由中央黨部、司法院、考試院聯合舉辦中央黨務工作人員參加甲種司法官特種考試[10]」,也就是國民黨決定、國民黨主辦、給國民黨黨工參加、考過了就是司法官。而姚瑞光說起此事面無愧色,可見黨派政治滲透司法的程度。二戰之後,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執政仍以「黨化司法」為政策,但轉為低調的潛規則,不再宣揚。劉恆妏指出,「黨化司法」在中國即「在司法體系中,安插、建立起一支屬於國民黨『自己人』的忠貞行伍」,二戰之後到台灣司法體系任職的,也都是這支「忠貞隊伍[11]」。翁岳生擔任大法官後,即使一再推辭,仍不得不參加國民黨為黨內政治人物加強聯繫而設的「國建班」,國民黨亦一再邀請他競選中常委[12]。
國民黨對司法的滲透,在第四屆大法官身上仍然持續。例如他們在討論釋字150號要不要受理的時候,涂懷瑩就說:「本案本可以其為政治問題不受理,但如此則將與中央決策不能配合,要發生新的問題[13]。」輕輕的一句話透露出很多訊息:「中央」是有意見的,有管道可以告知大法官;大法官對於政治力量的介入習以為常,於會議中不帶批判意味地公開說出,並且自我告誡、也可能是互相告誡:不配合的話就會「發生新的問題」。
林紀東是大多數大法官的老師。林紀東在國立中央大學[14]任教時,范馨香是他的學生;林紀東在中央政治學校任教時,楊與齡是他的學生[15];林紀東在台灣大學任教時,馬漢寶是他的學生[16];林紀東長年在司法官訓練所授課,所以法官、檢察官出身的大法官都是他的學生;馬漢寶、陳樸生、姚瑞光、鄭玉波、翁岳生、楊日然等人,不論年紀長幼,都是林紀東任教於台大法律系的後進學者。不過多位大法官的訪談回憶都提及林紀東為人謙和,並不倚老賣老[17]。
依照當時的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》,解釋憲法時需大法官總額四分之三出席,出席人四分之三之同意,方得通過。也就是至少12人出席,至少取得9票。但戒嚴時期並不鼓勵個人意見,而鼓勵集體性、「犧牲小我完成大我」,司法文化亦深受影響,大法官之間崇尚妥協,絕不「傷了和氣」;例如陳樸生會在自己意見與多數不同的時候藉故離席,避免自己成為多數意見的絆腳石[18],而馬漢寶也自承「我經常是因為顧全大局,所以很少寫不同意見書[19]。」
大法官一週開一次審查會。當時司法院長、副院長都不是大法官,審查會由16位大法官輪流當主席,討論與表決均完畢後,才將案子提到院會,由司法院長主持,並最後確認。在審查會前,大部分的大法官會開「會前會」,通常在范馨香家進行。大家交換意見以後,由翁岳生與范馨香去向較年長、較資深的大法官溝通,翁岳生形容林紀東「特別親切,不好意思反對我們的意見,非常好溝通。他總是笑著說:『我的意見好像都被你們牽著走了[20]!』」
翁岳生認為1976年上任的第四屆大法官是「釋憲功能發揮的轉捩點」,因為此時台灣社會經濟快速發展、中產階級興起、民眾權利意識提升[21]。不過,1979年審檢分隸的爭議裡,翁岳生自述當時極力爭取的心境:「心想我不一定要當大法官,那個時候大法官也沒有什麼作用[22]」。綜合起來,若說第四屆是違憲審查權之甦醒,勉力將戒嚴體制之下冰封多年的憲法稍加解凍,庶幾近矣。
當年的大法官釋憲實務,至少有三個與今日相異之處,不可忽視。其一是政治對司法有常態性的、深刻的、實質的影響力。其二是從眾的壓力非常大,個體的意志經常受制於集體而無法表達或無法貫徹。其三是威權時期法治不完備,釋憲結果未必能落實(例如釋字86號審檢分隸一案,就是釋憲被忽視的惡例),也缺乏社會能見度與社會支持度(例如釋憲的媒體報導篇幅不如監察委員的調查報告)。綜合上面三個因素,應當可以理解大法官發言時謹小慎微,不直抒胸臆,而總是意在言外。因此,詮釋時需要仔細解讀其微言大義與弦外之音,並不忘考量政治干預的可能性。
======
[1] 直接挑戰「死刑是否違憲」是以刑法第33條為釋憲標的,如果這一條違憲,則所有刑罰種類中不可再有死刑。憲判八載明刑法第33條不在受理範圍內,迴避了這一問題。
[2] 「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案件工作天數一覽表」見翁岳生,〈憲法之維護者〉,收於《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(第六輯) (上冊)》,頁147-166;https://publication.iias.sinica.edu.tw/book/book08/book08ch01-2/files/assets/basic-html/index.html#1。例如釋字166號解釋從收案到公布解釋,竟耗時7079天。
[3] 〈楊與齡先生訪談記錄〉(2004),頁77。《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》第一輯,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著,台北:司法院。
[4] 鍾榮吉,〈大法官人選具備四項特色〉,1976年9月9日,《聯合報》第二版。
[5] 馬漢寶自述,出任大法官一職是經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告知,見〈馬漢寶先生訪談記錄〉(2006),《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》第二輯,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著,台北:司法院,頁119。
[6] 1976年9月9日《聯合報》第一版。
[7] 〈楊與齡先生訪談記錄〉(2004),頁79。《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》第一輯,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著,台北:司法院。
[8] 〈馬漢寶先生訪談記錄〉(2006),頁123。《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》第二輯,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著,台北:司法院。
[9] 1929年6月17日國民黨第3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2次全體會議作出「關於司法制度之完成及其改良進步之規劃案—民國18年6月17日通過」,收於:秦孝儀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,革命文獻第79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(一),頁131(1979年);轉引自劉恆妏(2019),〈戰後臺灣的「黨化司法」——1990年代之前國民黨對司法人事的制度性掌控及其後續影響〉,《中研法學期刊》第24期,頁7。
[10] 〈姚瑞光先生訪談記錄〉(2004),頁6。《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》第一輯,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著,台北:司法院。
[11] 劉恆妏(2019),〈戰後臺灣的「黨化司法」——1990年代之前國民黨對司法人事的制度性掌控及其後續影響〉,《中研法學期刊》第24期,頁75。
[12] 翁岳生(2021),《憶往述懷:我的司法人生》,台北:遠流,頁272。
[13] 楊雅雯(2021),〈萬年國會的動搖跡象:釋字第一五〇號解釋檔案〉,《奉命釋法:大法官與轉型正義》,台北: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,頁243。
[14] 該校位於中國南京。
[15] 〈楊與齡先生訪談記錄〉(2004),頁45。《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》第一輯,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著,台北:司法院。
[16] 〈馬漢寶先生訪談記錄〉(2006),頁91。《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》第二輯,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著,台北:司法院。
[17] 〈梁恒昌先生訪談記錄〉(2006),頁76,《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》第二輯,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著,台北:司法院;翁岳生(2021),《憶往述懷:我的司法人生》,台北:遠流,頁272。
[18] 翁岳生(2021),《憶往述懷:我的司法人生》,台北:遠流,頁283。
[19] 〈馬漢寶先生訪談記錄〉(2006),頁120。《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》第二輯,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著,台北:司法院。
[20] 翁岳生(2021),《憶往述懷:我的司法人生》,台北:遠流,頁272。
[21] 翁岳生(2021),《憶往述懷:我的司法人生》,台北:遠流,頁279-280。
[22] 翁岳生(2021),《憶往述懷:我的司法人生》,台北:遠流,頁297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