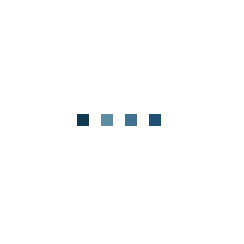孤獨散步者的夢想/教育工作者
柯文哲交保了,可以預期他不甘寂寞,遲早興風作浪。而小草們絕不會讓他唱獨角戲,更不會因某些循循善誘就放棄柯。會的話,草就不是草,柯也不是柯了。
但人們通常對涉貪的政治人物避之唯恐不及,小草為什麼能對柯文哲不離不棄?甚至柯一交保,民眾黨現任黨主席黃國昌立刻相形見絀到近乎消聲匿跡。可見民眾黨是標準一人政黨,唯一能凝聚支持者的就是柯文哲。所以要了解小草為什麼支持民眾黨,就要了解柯有什麼能吸引小草的人格特質。
柯文哲一開始是以亞斯伯格症(Asperger syndrome)、智商157、台大醫師、葉克膜之父的形象登上政治舞台的。這些綜合出來的形象是,靠後天努力克服先天障礙的高功能自閉症(High-functioning autism)患者。再加上台灣從日治時期以來對醫師與台大的正面形像,他的負面特質反而變成正面加分,甚至對某些人產生「我也可以做到」的激勵作用,進而對他產生認同。
自以為是神的柯文哲
柯曾接受《財訊》專訪,對於自己被神化的問題,他雖知道「所有人都不敢違逆他的意見,這就是作為一個神的危險」。但卻說「我雖然作為人間的神,至少他是有哲學修養的」、「是因為他從頭到尾都很清醒,才變成神」。言下之意頗為自負,認為自己較其他被神化的政治人物來得清醒與高明。
可見他雖然知道當神很危險,卻因認為只要清楚知道就能避免(認為知道就能控制,但知道與控制通常是兩回事),因此樂於沉溺於這種危險之中,並最終讓自己被這種危險所同化。不然要如何解釋他後來動輒以「朕」或「雍正」自稱?畢竟朕即天子,就是人被神格化後的產物。
亞斯伯格症與自戀型人格的重疊與差異
先不論自居於神是否僭越。比較有趣的問題是,什麼人會腦袋不清楚到把自己當成神?當然只有自戀到極致的人。很巧的是,自戀型人格(narcissistic personality)與亞斯伯格症有著高度重疊:它們都只關心自己、執著自我形像的、缺乏同理心……。但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:亞斯伯格症只在乎自己,不期待眾人眼光;但自戀型人格卻極需要眾人關注與喝采。而且亞斯伯格症之所以缺乏同理心,是因認知上無法理解他人,但在情感上仍會關心他人;但自戀型人格則只關心自己的需求,甚至會透過人際關係使自己得利。
所以自戀所愛的絕「不只」是自己,它愛的其實是社會價值對自己的認同。因而它絕非孤芳自賞,而是冀求活在眾人的掌聲中。就像直播顯示的,表面上似乎是直播主對自身影像的迷戀與執著,事實上卻是因他人對這個影像的認同、讚賞與否,而形成某種評判標準,進而使直播主逐漸認同、甚至化身為這個標準。
所以為了繼續活在這些掌聲中,自戀者會由開始被動回應,進展到主動迎合討好。就像柯文哲從頗具清譽的台大教授和醫師,竟能毫無困難的轉身成在辦公室一邊踩飛輪,一邊對送錢者說謝謝的政客;甚至不在乎降低自己的格調,能和滿身剌青、滿嘴髒話的館長並肩共處。這就是因為他已經從被動回應到主動地配合,甚至期待某些人的眼神與掌聲,以及其背後特定的社會價值。
一群認為社會亂象來自於自己不受重用的憤青
但這些人為什麼會讚賞柯文哲?一般而言,被讚賞代表的是被認同,也就是已達到自己所希望達到的標準。因此認同一個人,就是覺得他和自己在本質上一樣,只在程度上有分別;而現在的他,就可能是將來的自己。換言之,讚賞自戀者的人和自戀者一樣,都期待活在別人掌聲裏,也都覺得自己被認同與讚賞的程度遠遠不夠,還需要更多。
換言之,他們的共同特色都是覺得自己「應該」被賞識與重用,並認為就是因為自己未被充份重用,當下的社會才會亂成這幅模樣,並為此而憤憤不平。而為了讓自己被賞識,他們會不斷誇大自身的重要性,進而產生與現實相背離的幻想,譬如認為自己即將被某大人物所重用(黃國昌曾說如果小英找他去當法務部長該怎麼辦)。而由於只關心自己,就因而經常會覺得別人嫉妒他(但其實是他嫉妒別人,就像柯看著法院監視器卻能幻想賴清德在另一頭監視他)。並認為他人必須無條件順從自己,而經常表現出傲慢與不屑。
由於這群人都覺得自己該受重用卻沒人賞識,自然會從同病相憐到相互肯定。但這種沒有專業治療師參與的團體心理治療,會不會導致症狀的固著而非緩解?而且自戀型人格與反社會人格(antisocial personality)也有高度重疊,都只關心自己,但後者更懂得刻意操弄與精準算計,以便能夠迴避法律責任,以謀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
扭曲語言來弱化思想與操控對象
而這種精準的算計與刻意的操弄,具體表現在對語言的扭曲與操弄上。因為思想奠基於語言,對語言加以簡化、取消或取代,就會造成思想與表達的弱化,進而混淆對真假是非的判斷,而得以控制人們的行動。最有名的莫過於歐威爾(George Orwell)在《一九八四》裏所設想的「新語」(Newspeak):「戰爭即和平」、「自由是奴役」、「無知是力量」。或者《動物農莊》的「所有動物生來平等,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。」
但民眾黨還只會竄改字詞的原義。像原本強調以親身體驗擴大原先只限於文字理解的「走讀」,被操弄成對不合法「走」上街頭抗議的美化。「台灣民眾黨」(日治時期蔣渭水成立的第一個台灣人政黨)原來具有的團結台灣人之反抗與自主意識徹底消失,只剩權充民眾黨黨徽,那個大大的、活像烏合之眾的「眾」字。而通常用來做帳的Excel,裏面的 1500卻被扭曲成時間。無視公職人員不得收受現金或禮物饋贈,更無視證人承認送錢給具公職身份的柯文哲,用「你情我願」遮掩收賄事實,還攻擊證人「被植入記憶」。
這些詞語當然沒有專利。但把它們從脈絡中割離而任意挪用,就能達成扭曲語言、弱化思考,導致支持者變成隨聲附和的應聲蟲。更可怕的是,台北市長蔣萬安不制止「走讀」就算了,還助長這種風氣,將之解讀為「人權」活動,警察執法則是「沒有辦法」的選擇。難怪孔子說「巧言令色,鮮矣仁」,柏拉圖也嚴厲批評詭辯學派(sophist)。因為滔滔不絕的雄辯下,隱藏的是刻意扭曲的胡言亂語,與誤導群眾的不良意圖。
長此以往,對語言的刻意扭曲就會形成新型的思想瘟疫,社會就會變成貌似民智已開,實則高度弱智(人人都講的頭頭是道,但實則多是胡說八道),而危及對民主社會最重要的獨立思考,以及它所引發的自主且不盲從的行動。如此,社會就會被號稱為人民「指明方向」的獨裁者任意操弄,陷入分崩離析的高度危險中。而納粹已經示範過這種狀況。
漢娜.鄂蘭(Hannah Arendt)從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得到的結論是,艾希曼放棄獨立思考的責任與對自己良知的傾聽,這是一種「平庸之惡」(the banality of evil)。雖然鄂蘭因此遭到大量指責,說她為艾希曼開脫。但重要的是,她從未否認「平庸之惡」會導向大屠殺這種「根本惡」(radical evil),這種人類完全無法理解的,以暴力為唯一目的之暴力。而主導根本之惡的獨裁者所做的,不就是透過刻意的胡言亂語來弱化思考、誤導群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