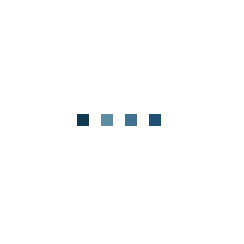我做狗仔多年,遇過各種場面,但那一次在圓山飯店的春酒偷拍,至今想起還是覺得像場黑白片——有點荒唐,也有點幸運。
事情發生2004年,《壹週刊》創刊第三年左右,那時候黑道比現在神祕很多,我們根本猜不透。我記得那天是四海幫在圓山辦春酒,場子在地下室,桌數幾十桌,場面不小。由幫主賈潤年主辦,入口那兒還排著一列小姐穿著旗袍站位,氣氛正式且熱鬧。
那天我們有好幾個人,兩個文字和我一起混進去,準備偷拍春酒的現場。我們全黑西裝裝扮和小弟差不多,設備是底片時代的「針孔攝影機」,一個是煙盒型,一個是公事包型,並沒有帶小相機。我的大相機則留在圓山外面的車上,另外還有兩個攝影在外頭待命,拍攝兄弟們進出的畫面。
進場時其實有點鬼使神差。我把煙盒型針孔攝影器材,放在窗框那邊,想趁著不被注意拍點畫面,結果正好被一個小弟看到。沒多久,有人就把我拖到另一個房間,本來想要打我,後來是個叫「平哥」的幹部發現,出面問話。
他問,我們是誰?想幹嘛?我說是《壹週刊》,想拍你們春酒。他再問,裡面還有你們的人嗎?我說,被你們發現的時候,我已經示意他們走了。他說,好,你現在去門口坐著,等我們開始之後,再商量要怎麼辦。他叫人把我帶出去、讓我坐在門口等。
我的文字同事已經走了,現場剩下我一個。不過,他們只發現煙盒是針孔,並沒有發現公事包也是針孔,所以,我就坐在門邊,用公事包針孔偷偷錄影進出的道上兄弟。
被帶到包廂時我有點緊張,但外表仍然裝作淡定,畢竟我們是來拍攝的。我跟平哥說:「我是來拍你們春酒的。既然被抓到,我就認了」對方倒也沒有立刻動粗——他先要了名片、讓我坐下,還倒了茶給我。
後來情勢慢慢緩和,「平哥」忙完了,問我們要怎麼拍?我說,我想拍你們盛大的場面,但我用針孔不能拍,我的大相機在外面,可不可去拿大相機進來拍?並請外面的攝影進來支援?結果,「平哥」露出一個「得寸進尺」、不可置信的表情。
「平哥」想了一下,最終表示可以拍攝,並要兩個小弟跟著我去外面拿相機。我們在外面的九人座的小巴裡,還有兩個文字及兩個攝影,當我打電話說,我要去拿相機,並要他們下來支援拍攝時,他們全嚇壞了,大叫要我不要去找他們。原來,早先社會組頭頭已經有跟對方溝通過,希望可以去拍春酒,但對方明說,我們可以在外面拍,但不要進到會場,只是,社會組長官事先並沒有告訴我們。
不過,現場場面那麼大,我一個人一定忙不過來,真的需要其他攝影協助,於是我和「平哥」派的兩個小弟,就一起走到九人小巴去拿相機,當我把小巴門打開之後,裡面同事全嚇了一大跳,他們沒想到,我真的把人帶過來了。
就在大家尷尬四目相望時,兩位小弟突然說,你們進去時,可以拍別人,但不要拍我們。後來,我們一共進去了兩個文字及三個攝影進去拍。我拿著廣角鏡頭,直接對著主桌的幫主一直拍,引來小弟的干涉,問我是哪裡的?當時,「平哥」就坐在後面一桌,我說,你去問「平哥」?結果,「平哥」就朝著小弟的頭巴下去。拍完後,我就拿了一杯酒去敬「平哥」,謝謝他。從那年之後,四海幫春酒突然變成媒體都會報導的新聞。
事後回想,我們運氣真的不錯,人家早就說,只能在門外拍,但沒人告訴我,結果,誤打誤撞,拍了個大獨家。而且,那次還是四海新幫主「弟哥」初登場的日子。後來,我還看到藝人吳宗憲出現在舞台上唱歌,我立即拿起相機來拍,結果,吳宗憲一看到,臉色大變。
週刊出來後,我們拍到的照片被大篇幅刊登,效果出乎意料地好。——後來,我們再去拍四海的聚會,就幾乎沒什麼問題。事後我們一群人趕快跑去吃豬腳麵線當作慰勞,——那是我們的壓驚儀式。
一直到前幾年,「平哥」名片我才丟掉,如今再看那組相片,不禁覺得那段時間我們既魯莽又幸運。魯莽的是帶著針孔就衝進危險場面,幸運的是最終沒惹出不可收拾的麻煩。那天,如果不是「平哥」把我帶去另一個房間,我應該會被小弟打得很慘。
這篇回憶並不是什麼英雄壯舉,只是想把那晚的荒謬與驚險留給年輕世代看。新聞不總是光鮮,拍攝背後常常是灰色地帶。但也正因為那些灰色,才有我們的故事,才有後來能笑著回想的豬腳晚餐。寫到這裡,老實說,我還是建議——年輕的同業,攝影器材可以升級,但膽識要跟著練;遇到危險,安全永遠第一,別把自己當成新聞的代價,否則可能再也吃不到豬腳麵線。(本文內容由當事人口述,AI協力完成,經編輯核實無誤。《狗仔回憶錄》每逢週六更新)